摘要:在制药领域,对提高疗效和减少副作用的需求不断增加,促进了制药领域创新和研究的新前沿:新型给药系统。这些系统旨在解决常规给药的局限性,如半衰期缩短、靶向性不足、溶解度低和生物利用度低。随着药学、材料科学和生物医学等学科的不断发展和融合,包括生物制剂在内的高效安全给药系统的开发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本文综述了药物传递系统的最新进展,根据其主要目标和方法,将其分为四个主要领域:基于载体和基于耦合的靶向药物传递系统、智能药物传递系统和药物传递装置。此外,它还批判性地分析了新型给药系统应用中的技术瓶颈、当前研究挑战和未来趋势。
1. 介绍
DDS代表了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技术进步,其被设计为以可控的方式和预定的速率释放药物,并将其递送至特定的组织或细胞类型。最近的药物递送系统,如纳米颗粒、分子印迹聚合物和3D打印技术,已经成为前沿研究课题。DDS是实现靶向和精确给药的关键策略。表1 简要介绍了与药物分子递送相关的挑战和解决方案。
通过利用多学科方法,DDS致力于开发能够调节药物的代谢、效力、毒性、免疫原性和生物识别的药物递送系统和装置,从而增强药物作用的微环境并促进其被身体吸收[1]。与常规制剂相比,DDS具有几个关键优势:(1)增强药物稳定性,减少降解;(2)优化药物分布,提高靶标浓度,减少不良反应;(3)精确的药物定位、定时和靶向释放,如突破血脑屏障的药物递送和(4)减少治疗剂量,降低毒性,提高治疗指数。DDS不仅将药物输送到受影响的区域,而且还包括四个核心功能:药物靶向、控制释放、增强药物吸收和改善药物稳定性。这些功能符合临床药物应用中最关键的需求。
表1. 药物分子递送的挑战和解决方案

对DDS的研究跨越多个学科,相互交叉、相互协作。本文从基于载体和基于偶联的靶向给药系统、智能给药系统和给药装置四个方面综述了DDS的最新研究进展,与给药系统的主要目标和方法相一致(图1).此外,对新型给药系统应用中的技术瓶颈、目前研究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图1. 给药系统的主要类型
2. 基于载体的药物递送系统
2.1.纳米药物传递系统(NDDS)
“纳米技术”最初于1959年提出[2],目前正经历着科学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它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的结合推动生命科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纳米技术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由此产生的纳米制剂有望在生物医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应用纳米技术构建给药系统,可有效提高药物的溶解性、稳定性和肿瘤靶向性,减轻毒副作用[3]。在NDDS的构建中使用了各种材料,包括脂质体、纳米药物、聚合物胶束、水凝胶和无机纳米药物递送系统[4,5]。
2.1.1. 脂质体
脂质体的特征在于其有序的脂质双层形成封闭的囊泡,具有疏水壳和亲水核,粒径范围为20至1000nm[6, 7]。由于其独特的组成和结构,脂质体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以正常代谢。因此,它们可以增强药物溶解度并减轻药物毒性[8-10]。脂质体能够同时包裹亲水性和疏水性药物[11],从而保护药物不被降解,防止药物在其他组织和器官中蓄积[12](图2)。基于纳米技术的脂质体给药系统的发展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才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这一进展促进了抗肿瘤、抗细菌感染药物和疫苗的发展。例如,在抗癌剂白藜芦醇的情况下,与游离白藜芦醇相比,利用固体脂质纳米颗粒递送白藜芦醇导致Wistar大鼠脑中白藜芦醇浓度显著增加,表明对脑肿瘤的高渗透性和最小的全身毒性[13]。

图2. 脂质体给药系统的亲水和疏水结构
在肿瘤治疗中,脂质体包裹的放射增敏剂可以增强对肿瘤部位的X射线辐射。Zhao等人[14]设计了一种抗原捕获钉状脂质体(ACSL),该脂质体具有坚固的结构和生物活性表面,能够捕获肿瘤相关抗原(TAA)并将其从溶酶体转运至树突状细胞(DCs)的胞浆,从而增强TAA的交叉呈递,并在局部照射后诱导T细胞依赖性抗肿瘤反应和免疫记忆。包裹抗癌药物阿霉素的脂质体显著降低了与阿霉素相关的心脏毒性,并减少了不良反应的发生,包括骨髓抑制、脱发、恶心和呕吐[15]。研究表明,通过薄膜分散-超声法制备的癸氧喹酯纳米脂质体(DQNLS)的抗球虫活性显著增强[16]。
脂质体是促进药物透过血脑屏障的一种普遍策略。转铁蛋白修饰的脂质体具有高效的药物转运能力。在神经胶质瘤荷瘤小鼠模型中,脂质体的治疗效果表现出最小的全身毒性和非侵入性全身给药后神经胶质瘤的显著消退[17]。地衣多糖脂质体与利福平联合治疗耐多药结核病,显著增强了利福平的抗菌活性[18, 19]。C型凝集素病原体识别受体DC-SIGN的碳水化合物识别结构域(CRD)可被抗真菌脂质体特异性靶向,从而增强脂质体两性霉素B(AMB)在体外和体内的抗真菌功效[20]。
脂质纳米颗粒(LNPs)代表了脂质体递送系统中的关键技术,并已成为基于寡核苷酸的治疗剂领域中的实质性进步。LNPs是一种没有亲水性空腔的特殊脂质体,由阳离子磷脂和带负电荷的核酸成分组成,它们通过静电复合,形成散布在脂质层之间的多层核心。包封在LNP内的寡核苷酸在递送过程中受到保护,保持完整且不被酶降解,并有效地递送至细胞,其中载体颗粒的内容物被释放并翻译成治疗性蛋白。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公布了一项突破性的策略,称为选择性器官靶向(SORT)。这种创新方法涉及将SORT分子整合到不同的LNP阵列中,从而实现肝外组织的精确靶向[21, 22]。SORT与各种基因编辑技术的协同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基因治疗领域的发展,特别是那些针对特定组织内蛋白质的基因治疗。Shuai等人[23]开创了一种新型LNP递送系统(IPLNPs),该系统结合了具有增强细胞内吞逃逸能力的新型磷脂(IPHos)。通过控制IPHOS的化学结构和比例,可以非常精确地实现器官选择性递送。在另一项研究中,Min等人[24]鉴定了一种新的LNP变体,其尾部具有酰胺键,可以通过调整其头部结构来微调以靶向各种肺细胞类型。202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给心力衰竭小鼠注射了包裹在LNPs中的mRNA,有效地修饰了T细胞并恢复了它们的心脏功能。在这一成功的基础上,2023年,他们开发并合成了可电离的LNP,其能够将mRNA递送至胎盘,而不会进入胎儿室,这可能为妊娠并发症(如先兆子痫)提供新的治疗途径[25]。在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利用基因编辑的力量,从患者来源的T细胞中创造出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26]。在LNP递送系统的推动下,这一尖端技术确保了封装的CAR基因可以通过细胞核定位进入细胞核,使其成为一种新兴的、有前途的癌症治疗方法。修饰的mRNA靶向LNP在减少纤维化和恢复损伤后的心脏功能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潜力,同时还在体内产生短暂但有效的CAR T细胞。这些CAR T细胞作为治疗多种疾病的多功能治疗平台具有巨大的前景[27]。在解决外源mRNA穿透细胞质而不被核酸酶降解的挑战中,Covid-19 mRNA疫苗普遍使用脂质纳米颗粒(LNPs)作为其递送载体。这一创新显著提高了疫苗的效力、稳定性和安全性[28]。事实证明,纳米聚合物技术可减少网状内皮系统(RES)对 LNPs 的吸收,从而提高包裹人促红细胞生成素(hEPO)mRNA 或因子 VII(FVII)siRNA 的 LNPs 的生物利用度。这导致hEPO产量(32%)或FVII沉默(49%)显著增加[29]。此外,Swingle及其同事已经开发了一种可电离的脂质,专门用于配制LNP,用于将mRNA递送至胎盘细胞。包裹VEGF-A mRNA的领先LNP制剂诱导胎盘血管舒张,突出了mRNA LNP作为蛋白质替代疗法治疗妊娠期间胎盘疾病的潜力[25]。
此外,微生物群移植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关键策略。然而,口腔细菌疗法的发展受到生物利用度低和胃肠道滞留不足的限制。脂膜包被细菌(LCB)是一种通过生物界面超分子自组装包裹肠道微生物的简单而高效的方法。用额外的自组装脂质膜包裹的细菌已经证明在环境挑战中显著增强了生存能力,而生存能力和生物活性的变化最小。此外,它们提高了口服给药在两种结肠炎小鼠模型中的治疗效果[30]。脂质体作为迄今为止临床应用中研究最广泛和最成功的纳米载体,具有低毒性、优异的生物降解性、无免疫原性以及保护包封药物不被降解的能力[31]。然而,脂质体仍存在载药量低、稳定性差、生产成本高、潜在毒副作用、在肿瘤部位蓄积变异性大等缺点[32]。LNP给药系统未来的研发方向主要集中在提升对内外刺激(如温度、超声、酶等)的靶向性和响应性,从而实现精准治疗[33]。
2.1.2. 球囊体(Tocosome)
生育体是一种复杂的胶体和囊泡生物活性载体系统,主要由维生素E的衍生物α-生育酚磷酸酯(TP)组成。维生素E天然存在八种不同的形式,其中α-生育酚是最普遍、最丰富和最具生物活性的。TP因其窄的粒径分布、值得称赞的包封率、最小的免疫原性、优异的生物相容性以及增强的溶解和渗透能力而脱颖而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延长其稳定性[34]。生育酚的多方面属性使其成为药物输送系统工程中的一种适应性成分。类似于脂质体,由形成双层胶体结构的两亲分子组成,尽管其化学成分独特,但在药物递送机制和释放模式中表现出类似的行为[35]。
临床研究强调了TP的众多健康优势,包括其在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心脏保护、抗炎作用和抑制肿瘤转移中的作用[36-38]。除TP外,生育酚制剂还含有各种磷脂和胆固醇组合,这些组合已被有效用于抗癌药物5-氟尿嘧啶的包封和控制释放[34]。
苹果酸舒尼替尼和甲苯磺酸索拉非尼都是转移性肾癌的靶向治疗药物,通过不同的途径发挥作用,以阻止血管生成和肿瘤增殖。Fariba及其同事采用Mozafari方法[39, 40],通过将壳聚糖(CS)与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Am)混合,率先开发了一种包衣生育胶囊。这种对温度敏感的胎体纳米载体具有增强的稳定性、理想的粒径和工业规模生产的潜力,使其成为抗癌药物苹果酸舒尼替尼和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的一种有前途的、强大的药物递送系统。
Tocophersolan(TPGS)是一种独特的多向聚合物,是维生素E的聚合合成衍生物。TPGS已被FDA批准为一种安全的药用辅料。紫杉醇和多西他赛(DTX)是一类高效、低毒、广谱的天然抗癌剂,主要用于治疗卵巢癌、乳腺癌和支气管癌等。它们的作用模式包括通过促进微管组装和防止微管分解来抑制癌细胞生长[41]。Qi等人[42]用胆固醇修饰TPGS以产生新型载体材料TPGS-CHMC,其具有较低的临界胶束浓度(CMC)。TPGS-CHMC降低紫杉醇耐药卵巢癌细胞(A2780/T)线粒体膜电位和细胞膜流动性。在A2780/T荷瘤裸鼠中,与游离DTX溶液相比,TPGS-CHMC/DTX胶束表现出显著增强的抗肿瘤功效和降低的毒性。
2.1.3. 聚合物纳米粒子
聚合物纳米颗粒(PNP)是直径为10至1000 nm的胶体颗粒[43]。粒径较大的脂质体不易穿过内皮细胞层或血脑屏障,而粒径较小的PNP则易于穿过这些屏障到达靶位点。常见的PNP包括合成聚合物,如聚乳酸、聚(丙交酯-共-乙交酯)(PLGA)、聚氨基酸和天然聚合物,如壳聚糖、藻酸盐、明胶和白蛋白[44]。研究表明,PNP药物递送系统可生物降解,能够降低全身毒性和刺激性,延缓药物降解,改善药物释放动力学,增强生物相容性、药物安全性和疗效[45, 46]。控制聚合物的降解/断键也可以调节体内释放动力学并促进体内递送载体的清除。
纳米药物的表面聚乙二醇化显著延长了其在血流中的循环时间,并增强了其渗透性和保留(EPR)效应。因此,开发了一种依赖于偶氮键的热分解的近红外(NIR)光触发的去聚乙二醇化/配体呈递策略。该方法涉及由热不稳定偶氮分子连接的长PEG链聚合物(PZ-IR)、具有短PEG链的CRGD共轭IR783(RP-IR)和阿霉素自组装DOX/PZ-IR纳米颗粒。DOX/PZ-IR纳米颗粒通过进行性肿瘤积聚、精确调节的光热效应和NIR-光热疗法(PTT)诱导的脉动药物释放,在温和温度下实现光热化疗的最佳协同效应[47]。Van de Ven等人[48]利用PLGA作为载体材料和两性霉素B制备载药纳米粒,证明在体外没有明显的溶血毒性,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抗真菌作用。
克服血脑屏障(BBB)的调节屏障将药物输送到大脑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研究挑战。一种策略是使用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并将治疗分子递送到大脑特定部位的纳米药物(图3)。

图3. 纳米药物穿过血脑屏障并将治疗分子输送到大脑中的靶位点
树枝状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树枝状结构的大分子,它是由低聚物通过支化单元重复线性连接而形成的,在这方面显示出了良好的前景。羟基聚酰胺胺(PAMAM)树状大分子可以穿过血脑屏障和血脑脊液屏障,有效地将小分子药物递送到靶位点,特别是在损伤的脑组织中[49]。与大小为4.3 nm的PAMAM树状聚合物相比,大小为6.7 nm的PAMAM树状聚合物表现出更长的血液循环时间和更大的脑内积聚[50]。此外,具有阳离子表面性质的PAMAM树枝状聚合物在颈动脉给药后可穿过血脑屏障并定位于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中[51]。
壳聚糖作为真菌膜上的一种独特受体,已被Tang等人[52]利用开发包裹伊曲康唑的壳聚糖结合肽修饰的PLGA纳米粒。这些纳米颗粒具有识别真菌表面壳聚糖的独特能力,从而对新型隐球菌产生显著的靶向作用。此外,用鼠李糖脂(RL)修饰的壳聚糖纳米颗粒已经负载了抗微生物植物化学物质异甘草素(ISL)(ISL@RL-CS)。该制剂能够在所有阶段同时消除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生物膜,并减轻相关炎症[53]。
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研究人员最近公布了一种基于岩藻多糖的纳米载体,其靶向内皮P-选择素,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包裹小分子抗肿瘤药物vismodegib的纳米颗粒通过P-选择素介导的转运有效递送至脑肿瘤组织,显著增强了药物的治疗效果[54]。
分子印迹聚合物(MIP),也称为“合成抗体”,是通过分子印迹技术(MIT)制备的。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基本概念包括通过共价或非共价相互作用形成模板分子-功能单体复合物,然后在交联剂存在下聚合,最终去除模板分子以产生在大小、形状和化学亲和力方面与模板匹配的结合位点或空腔[55]。由于分子印迹聚合物对模板分子的精确选择性和亲和力,可以实现药物的持续释放。
槲皮素(Quercetin,3,3,4,5,7-pentahydroxyflavone,QC)是一种强效抗癌剂,通过上调内源性自由基防御、抑制肿瘤发生和肿瘤进展信号通路发挥其抗氧化作用。然而,槲皮素的疏水性、胃肠道吸收差以及在肠道和肝脏中的广泛异源代谢限制了其在化学保护方面的临床应用。以黄蓍胶(TG)为交联剂,Fe3O4/SiO2纳米粒子和N-乙烯基咪唑(VI)功能化单体为模板,采用溶胶-凝胶法合成了具有核壳结构的高选择性磁性分子印迹聚合物(MMIP)。由于TG的存在,合成的mMIP纳米凝胶是生物相容的,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易于分离,并能特异性识别模板QC[56]。因此,MIP和mMIP材料有望作为聚合物装置应用于快速药物分离和药物递送。
多糖纳米粒(PNPs)在药物递送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其作用机制、环境相互作用、活性分析和复合材料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对其潜在毒性、聚合物稳定性和药物递送机制的探索仍未完成[57]。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未来的研究必须对聚合物纳米给药系统的药代动力学、安全性、免疫原性和其他关键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这将能够有效地调节这些系统的物理化学性质。
2.1.4. 聚合物胶束
目前广泛使用的聚合物胶束是由两亲性嵌段共聚物在水环境中形成的胶体聚集体[58]。它们以其结构完整性、疏水性药物增溶能力和最小毒性而著称。这些胶束的粒径范围为10至100 nm,可以逃避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作用,从而延长其全身循环时间[59]。此外,胶束的亲水性外壳不仅可以防止药物在血清中流失,还可以抵抗补体系统的激活,这可以在药物发挥作用之前过早地快速清除药物[60]。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聚合物胶束已被广泛用作高效、高毒性和难溶性小分子药物的载体[61]。值得注意的是,在抗真菌治疗领域,Albayaty等人[62]开发了一种用于包裹伊曲康唑的酸碱响应性胶束系统,该系统具有较高的药物负载能力,对白色念珠菌生物膜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可显著抑制其活性。聚胶束还具有装载多种化疗药物的组合用于靶向肿瘤递送的潜力,从而减少化疗相关的不良反应并提高胰腺癌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这项创新解决了化疗中的关键挑战[63]。Zhang等人开发的胶束[64],称为CELA/GCTR,具有显著的特性,使其成为治疗肝细胞癌中递送疏水性抗肿瘤药物的有希望的候选者。这些胶束在血流中表现出持续释放,在肿瘤微环境中表现出快速释放。疏水性链段被策略性地置于纳米颗粒的核心以包裹疏水性药物,而亲水性链段形成外冠,在水环境中保持胶束的结构。通过将特定的配体连接到亲水性冠上,这些胶束可以通过胞吞作用穿过血脑屏障,并随后在细胞内破坏时释放其治疗物质。各种嵌段共聚物胶束,包括PAAPEG[65]、PLA-PEG、DGL-PEG、PTMC-PEG和PDSGM-PEG,已被证明可促进治疗剂通过该屏障的转运。值得注意的是,负载紫杉醇(PTX)并用T-LYP1配体修饰的PLA-PEG胶束在神经胶质瘤细胞中的积聚和内化增强,在动物模型中有效抑制肿瘤进展[66]。此外,由PEG接枝的聚(2-甲基丙烯酸二异丙酯)(PDPA)共聚物(MPEG-B-PDPA)组成的高级蠕虫状聚合物胶束已被设计为响应脑肿瘤微环境的变化而降解,从而将药物直接释放到靶肿瘤中[67]。
胶束也广泛应用于传统中药制剂中,能够精确控制大黄素、姜黄素、黄芩苷和紫杉醇等成分的粒径、包封率和载药量,确保缓慢和持续释放。然而,由于中药提取分离过程中产生的单体分子尺寸微小,目前其应用主要局限于单体的合成,对中药提取物直接转化为胶束的研究有限[68]。
在国际上,基于聚合物胶束的药物已经获得上市许可,而在国内,这类聚合物胶束药物仍在进行临床试验。尽管在临床应用期限和制剂开发的长期安全性评估方面存在限制,但聚合物胶束的众多优势将推动其在疏水性药物递送中的不断增强和广泛应用。
2.1.5. 水凝胶
水凝胶是物理或化学交联的聚合物网络,具有在水存在下溶胀并与某些有机溶剂相互作用的独特能力[69]。水凝胶纳米给药系统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降解性和低毒性,有利于靶向药物的缓释。
在肿瘤治疗的背景下,放射治疗后的抗肿瘤免疫应答通常不足,需要使用免疫佐剂来增强抗原呈递细胞的功效。Wang等人[70]设计了一种由近红外光激活的水凝胶纳米马达,能够穿透肿瘤组织并在细胞内释放药物,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激活能力,并通过光疗、化疗和免疫治疗的整合实现协同效应。软水凝胶为修复各种组织缺损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材料选择。Li等人[71]开发了一种抗溶胀纳米纤维水凝胶,具有高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在伤口愈合过程中有效促进成纤维细胞迁移和加速血管生成。Sun等人[72]已经开发了一种创新的水凝胶纳米药物递送系统,该系统被设计为携带配体,该配体在用奥沙利铂或X射线照射治疗时与肿瘤细胞释放的ATP竞争性结合。该系统促进了免疫佐剂的释放,从而增强了治疗的协同治疗效果。
在兽医领域,Gao等人[73]已经设计了一种热敏凝胶疫苗递送系统,该系统表现出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可降解性和缓释能力。用重组质粒配制的新城疫温度敏感凝胶核酸疫苗已被证明可引发强大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应答,从而增强机体的抗病毒防御能力并延长免疫保护期。最近,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创造了一种创新的超分子纳米纤维水凝胶(水凝胶RL),其中包含抗菌肽。体外研究表明,水凝胶RL具有缓释、生物相容性,并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表现出有效的抗菌活性。这一进展为对抗多重耐药菌和解决慢性伤口感染导致的愈合停滞带来了希望[74]。
水凝胶系统在胃肠道中的抗降解性允许持续的药物释放。Azad等人已经观察到具有水凝胶性质的藻酸钙珠粒在胃中保持未降解并在肠道中释放。此外,其强粘附性有助于改善药物在肠粘膜中的滞留[75]。然而,到目前为止,口服水凝胶系统在临床试验中还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进展,这主要是由于在口服给药过程中,水凝胶在与大量肠液接触时迅速崩解。这个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中集中关注[76]。
水凝胶纳米给药系统在调节药物释放动力学、实现药物的远程和可控释放以及促进药物的位点特异性靶向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优势。然而,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仍然存在挑战。目前关于药物在水凝胶中释放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体外实验或严重依赖于肿瘤的内部微环境。评估水凝胶在体内植入后是否保持其响应特性将是水凝胶纳米药物递送系统的关键研究重点[77]。此外,水凝胶的开发需要对水凝胶药物递送载体的性质和在各种触发条件下的释放动力学进行更精确的控制。显然,高度可控和精确可调的水凝胶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应用潜力[78]。
2.1.6. 金属和无机纳米粒子
在纳米药物递送系统领域,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从金属或无机材料合成的金属和无机纳米颗粒代表了多样化和有前途的类别。这些纳米材料因其特殊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而与众不同,包括高比表面积、增强的生物利用度、低毒性以及与大多数有机溶剂的相容性,因此,它们在肿瘤的联合治疗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79]。纳米氧化物、碳纳米管、介孔二氧化硅、钙基纳米材料、磁性纳米粒子、铜纳米粒子和金纳米粒子都是重要的金属和无机纳米载体,它们不断推动着纳米医学领域的发展。
赵等人[80]已经将铜离子和其他物质整合到氧化应激放大器中,从而通过化疗使免疫疗法变得敏感。这种方法逆转了免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增强了免疫治疗的疗效,并显著抑制了原发性远端肿瘤的生长。他们的工作为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的联合治疗策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Gong等人[81]已经开发了磷和氮掺杂的空心碳量子点DOX载体,其已显示增强DOX的核内递送和肿瘤积聚,从而有效抑制肿瘤生长。设计用于寡核苷酸和多西他赛联合给药的多功能CuS纳米复合材料促进了TC细胞的浸润,并在与光热和光动力疗法联合使用时增强了乳腺癌的治疗效果[82]。
在兽医领域,Raposo等人[83]已经制备并测试了负载有钴和锌化合物的金纳米颗粒对犬癌细胞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纳米颗粒很容易进行表面修饰,并且在递送细胞毒性物质方面比游离化合物更有效。银已被证明作用于细菌酶和蛋白质,从而抑制细菌毒素的产生[84]。使用纳米技术制备的纳米银纳米颗粒(AgNPs),不仅具有纳米材料的特性,而且增强了银的抗菌效果[85]。银纳米颗粒(AgNPs)的潜在抗菌机制可能包括通过抑制细胞壁肽聚糖的合成来破坏正常细菌形态,以及通过抑制细胞分裂蛋白FtsZ和染色体复制起始蛋白DNAA来抑制细菌生长[86]。
畜禽粪便是大量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的储存库,畜禽粪便在土地上的积累可能会促进抗生素抗性细菌的出现和ARGs的传播。纳米零价铁(NZVI)具有广阔的表面积和独特的理化性质,可以有效降低抗生素的浓度,减轻堆肥过程中Arg传播的风险[87]。此外,铜纳米颗粒在预防和治疗乳腺炎方面均显示出疗效[88]。
无机纳米颗粒的反应性需要用生物相容性材料进行表面修饰,以用作非侵入性纳米药物。其中,金纳米粒子由于其易于合成、表面修饰能力和高生物相容性,是生物医学应用中最广泛使用的无机纳米药物。研究表明,金纳米颗粒可以利用内涵体内的可裂解键来促进穿过血脑屏障的运输,同时抑制血液回流。
Rodrigues等人[89]将转铁蛋白(TF)和狂犬病毒糖蛋白(RVG)肽结合到脂质体表面,靶向转铁蛋白和烟碱乙酰胆碱受体。他们使用体外三重共培养血脑屏障模型描述了这些脂质体在穿越血脑屏障中的功能。在体外血脑屏障模型中,发现脂质体RVG-TF可持续转染并有效转运原代神经元细胞,并观察到其在体内可增强血脑屏障的穿透性。Wang等人[90]制备转铁蛋白修饰的脂质体(TF-PL),用于将乙酰胆碱酯酶(AChE)治疗基因靶向递送至肝癌细胞。这些脂质体显示出比Lipo 2000更高的转染效率,并且在体外对肝癌SMMC-7721细胞显示出更好的靶向效果。此外,皮下注射TF-PL/AChE可显著抑制裸鼠肝癌移植瘤的生长。Lu等人[91]设计了一种具有液相共晶镓铟核和硫醇化聚合物壳的核壳纳米球。这种创新的纳米药物是一种可转换的液态金属系统,能够在弱酸性条件下融合并随后降解。这种机制有利于多柔比星在细胞内化后在酸性内体中释放,从而增强了异种移植肿瘤小鼠的化疗效果。
虽然无机纳米材料可以精确定制以满足各种药物递送要求,但其毒性、生物分布和体内清除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为了加快无机纳米药物传递系统的临床应用,未来的研究应优先研究药物在体内的滞留效应和增强药物的清除过程。
2.2.仿生给药系统
传统的药物载体经常受到不理想的生物分布、缩短的血液循环时间和降低的递送效率的困扰。纳米结构药物载体具有改变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生物分布的潜力。然而,它们容易被网状内皮系统识别为外来实体,这会阻碍它们到达预期的靶位点[92,93]。随着纳米技术、生物耦合和生物工程工具的不断进步,研究人员对自然物质(如细胞和病原体)与人体细胞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种理解促进了模拟这些结构和功能用于治疗应用的努力[94]。因此,研究具有最小毒性和强大生物相容性的内源性载体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利用生物载体如细胞、细胞外囊泡、病毒和细菌的仿生药物递送系统已成为药物递送领域的焦点。
近年来,基于细胞、细胞外囊泡、病毒、细菌等生物载体的仿生药物传递系统成为药物传递领域的研究热点[95]。生物载体继承了原始供体的结构和功能,作为内源性物质减轻不必要的免疫反应并逃避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的直接清除。此外,这些载体还可以在体内模拟高传染性因子或病原体的结构,复制其内部过程或作用机制,并确保将药物精确输送到目标部位,以获得最佳治疗效果。因此,生物载体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靶向给药系统[96]。
2.2.1. 细胞膜递送载体
细胞膜递送载体代表了一种迅速发展的、多方面的药物递送系统。它保持了类似于体细胞的膜结构,提供了优越的生物相容性和最小的毒性,这赋予了它与其他药物递送载体相比无与伦比的优势[97]。基于细胞的药物递送系统可以在膜蛋白和完整膜结构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容易地制造,从而赋予载体多种生物功能和靶特异性[98]。由于其独特的属性,如延长的循环时间、可适应的形态、低免疫原性和精确的靶向性,它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药物递送载体[99]。源自各种天然细胞和杂合细胞膜的仿生纳米系统已经证明了其在有效管理靶向药物递送系统方面的功效。这些系统可以降低免疫系统的清除率,延长血液循环时间,增强药物负载和靶向性,从而扩大对肿瘤的治疗效果[100]。
目前,用于细胞递送的主要载体包括红细胞、血小板、各种白细胞、干细胞和癌细胞。其中,红细胞给药系统以其丰富的原料和强大的靶向能力,通过其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展,在多种疾病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01]。Cao的团队利用红细胞膜开发了细胞膜细菌(CMCB),其作为强大肿瘤显像剂的潜力已通过各种小鼠模型的评估结果得到证实[102]。手术切除后,血小板在伤口处聚集,导致肿瘤微环境发炎,起到修复作用。Wang等人[103]将抗PDL1单克隆抗体偶联至血小板表面,在血小板活化过程中通过血小板衍生颗粒有效释放抗PDL1,从而减少术后肿瘤复发和转移。
包被在T细胞膜上的纳米颗粒含有对结合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至关重要的T细胞表面抗原,其可以模拟宿主细胞功能以中和病毒。作为抗HIV感染的新型治疗剂,它们显示出巨大的潜力[104]。近年来,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因其能够修饰患者自身T细胞以识别肿瘤抗原并激活局部细胞毒性免疫反应而出现在各种DDS中。Ma等人[105]发现CAR-T细胞可特异性识别肿瘤相关抗原,CAR-T膜包裹的NPs可用于肝癌的高特异性治疗。虽然CAR-T细胞疗法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成功,但治疗时间长、费用高等问题限制了其在B细胞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发展。在他们的开创性工作中,Agarwalla等人[106]描述了一种设计用于T细胞工程和释放的可植入多功能藻酸盐支架(MASTER)。这种创新的支架促进了CAR-T细胞的快速生成,使其能够部署到血流中,以调节远程肿瘤的增殖。这样的发展有望简化这些疗法的实施,从而减轻通常与其管理相关的复杂性和资源需求。目前,CAR-T细胞疗法主要适用于B细胞癌,尽管其疗效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新的CAR-T细胞变体,称为合成酶武装杀手(SEAKER)细胞。这些细胞在与肿瘤细胞结合后,当与小分子前药偶联时,在体外和体内环境中表现出增强的抗癌功效[107]。
已知巨噬细胞和其他吞噬细胞的细胞膜具有模式识别受体,其可以识别和识别病原体,并作为靶向药物递送的天然配体。Li等人[108]用巨噬细胞膜包裹胶原基纳米颗粒,从而增强生物相容性,增强纳米颗粒在感染部位的积聚,并增强抗菌功效。肿瘤细胞膜具有固有的肿瘤靶向能力,Guo 等人[109] 利用这一特性,创造了包裹肿瘤细胞膜的仿生物纳米粒子(gct@cm NPs),从而实现了肿瘤特异性靶向。Harris等人已经证明,包裹在癌细胞膜(CCM)中的纳米颗粒表现出屏蔽和靶向的双重机制,修饰的药物递送系统优先被肿瘤细胞内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肝细胞的摄取[110]。
Huang等人探讨不同细胞膜包裹的纳米载体作为靶向递送siRNA的潜在临床应用价值。与外泌体和其他递送系统相比,这种方法已证明有效。值得注意的是,仿生细胞膜涂层纳米技术成为癌症治疗中靶向siRNA递送的一种很有前途的策略[111]。
在细胞仿生药物递送系统中,天然细胞膜功能与纳米载体特性的整合为不同的应用提供了一条很有前途的途径(图4).这些细胞衍生的膜仿生纳米载体表现出延长的循环时间、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强大的免疫逃避能力。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纳米载体的毒性、生物分布和免疫反应。尽管如此,纳米载体的固有优势和细胞膜的丰富可用性为治疗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潜力[112]。

图4. 整合天然细胞膜功能和纳米载体功能的细胞仿生给药系统
2.2.2. 细胞外囊泡递送载体
在细胞外囊泡(EV)递送系统领域,这些由细胞释放的小囊泡含有生物活性分子,如蛋白质和miRNA。EVS作为生物相容性载体,具有固有的材料转运特性、低免疫原性和无细胞毒性或致突变作用。它们具有良好的循环稳定性、生物相容性、物理化学稳定性和穿越生物屏障的能力[113]。具体来说,巨噬细胞衍生的EV能够穿透血脑屏障,与癌细胞相互作用,并在其中积聚[114]。
自2013年以来,外泌体(exosomes)作为一种细胞外囊泡,尤其是直径在40~100纳米之间的外泌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这些由大多数细胞分泌的纳米级囊泡表现出固有的稳定性、生物相容性、最小的免疫原性和低毒性。其靶向特定细胞的独特能力使其成为生物医学应用的理想生物纳米载体[105]。此外,与正常组织相比,外泌体优先在肿瘤组织中富集。通过将肿瘤靶向配体与外泌体结合,可以实现特异性和靶向递送[115-117],促进蛋白质、肽、核酸和其他化合物通过各种途径(如静脉内、腹膜内、口服和鼻内给药)的递送。肿瘤来源的外泌体,当用作载体时,可以有效地靶向癌细胞,保护治疗化合物不被细胞外环境降解,同时还保持其生物相容性和低免疫原性[118]。树突状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富含抗原呈递和共刺激分子,能够激活T细胞,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功能,促进肿瘤的根除[119]。来源于免疫细胞的外泌体具有免疫调节特性和治疗潜力,在其表面表达各种抗原,这些抗原有助于抗原呈递、免疫激活和癌细胞清除的代谢调节,从而在癌症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120]。最近的研究表明,通过将细胞植入体内,可以产生定制的外泌体[121]。例如,将细胞植入活体小鼠体内产生的工程外泌体已被证明可持续向大脑输送mRNA,用于治疗帕金森病,这为在体内生产工程外泌体开辟了一条新途径[122]。
工程外泌体显著提高了治疗剂递送的功效和精确度,使其成为各种疾病(包括肿瘤、炎症和退行性疾病)靶向治疗研究的组成部分。这些工程化的外泌体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治疗剂装载、靶标修饰、逃避单核吞噬系统(MPS)吞噬、智能控制和生物成像,使其成为尖端的多功能纳米递送系统[123]。
与合成的纳米载体相比,细胞外囊泡给药系统在靶向性、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优势。然而,提取方面的挑战、低分离效率、高度异质性、有限的靶向能力和降低的细胞内药效目前阻碍了细胞外囊泡的临床应用[124, 125]。尽管处于研究的初期阶段,外泌体作为诊断生物标志物和抗肿瘤药物载体具有巨大的前景。此外,人造细胞外囊泡或细胞外囊泡模拟物已成为细胞外囊泡药物递送领域的焦点,因为它们具有无菌、大规模生产和易于调节的优点[126, 127]。
2.2.3. 病毒递送载体
病毒纳米粒子(Virus nanoparticles,VNP)是一类新型的纳米粒子载体,来源于噬菌体和动植物病毒。这些VNP的大小从10到1000nm不等,包括一些传染性品种。病毒感染细胞的固有能力突出了其作为递送载体的潜力。1977年首次实现了利用病毒作为载体的药物递送。病毒载体广泛应用于体内和体外药物递送研究,主要是由于其在基因递送和表达方面的卓越效率[128]。
目前,主要的病毒载体包括三大类:慢病毒(LV)、腺病毒(ADV)和腺相关病毒(AAV)。最广泛的应用领域是基因治疗,其中70-80%的基因治疗程序是通过病毒载体执行的。尖端基因编辑技术CRISPR在治疗先天性疾病和肿瘤方面具有重大前景[129]。2014年,Cheng等人开发了一种基于体内基因编辑的腺病毒CRISPR/Cas9系统,该系统应达到组织特异性基因敲除水平,导致表型改变[130]。
为了增强CRISPR药物递送系统的稳定性、细胞靶向和治疗效果,可以同时使用病毒和非病毒载体来合并两种载体类型的益处。例如,2016年,Yin等人[131]使用AAV载体递送sgRNA,而脂质体材料用于递送Cas9蛋白酶RNA。将两种载体联合递送至肝损伤小鼠模型,减轻了肝损伤症状,降低了CRISPR脱靶率。
随着生物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研究人员已经认识到蛋白质家族序列的多样性。直接在实验数据上训练的机器学习(ML)模型提供了一种利用工程蛋白质的全部潜在多样性的方法。布莱恩特等人[132]将深度学习应用于设计可以有效装载DNA的腺相关病毒2(AAV2)衣壳蛋白的变体,其在产生改进的病毒载体和蛋白质疗法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在超过90%的癌症的肿瘤间质中检测到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FAP)的表达,使其成为肿瘤特异性腺病毒递送的最佳靶位点。一个复杂的基因治疗平台,称为SHREAD(屏蔽,重新定位的腺病毒),已被精心设计为基于特定表面标记的选择性靶向细胞,有效地将其转化为能够分泌治疗分子的生物工厂[133]。人类腺病毒血清型5(Ad5)是一种流行的病毒载体,Hartmann 等人的研究表明,它可以在体外和体内重新靶向FAP+成纤维细胞[134]。
顾名思义,溶瘤病毒(OV)具有溶解肿瘤的独特能力。Wu等人[135]开发了一种用于隐蔽肿瘤靶向的新型病毒策略,其中用液氮休克处理OVS以消除致病性,实现靶向肿瘤递送并防止病毒在血流中清除。
虽然病毒载体提供了高转染效率,但它们并不是没有安全问题和有限的负载能力,这可能限制了大规模生产。去除非必需病毒基因以减轻毒性或构建自失活病毒载体等策略可以增强这些载体的安全性[136]。
2.2.4. 细菌递送载体
化学生物技术与细菌系统的融合为基于细菌的药物递送系统铺平了道路。例如,工程细菌由于其检测宿主生理和病理指标变化的显著能力,以及其优越的体内转运能力,被广泛用于靶向药物递送[137-139]。一些细菌表现出对缺氧微环境的倾向,使它们能够将药物输送到这种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140-142]。除了已知的相互作用外,真菌和细菌之间还存在特定的关联[143],例如,链球菌通过细胞表面多糖受体和肽粘附素和肽粘附素粘附于白色念珠菌。类似地,嗜酸乳杆菌和唾液乳杆菌可以通过多糖受体识别并与白色念珠菌共聚集,为开发靶向抗真菌药物提供了见解[144–147]。
Solomon等人我已经设计了一种用细菌囊泡包裹紫杉醇的递送系统,能够靶向实体肿瘤细胞中过表达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从而在异种移植模型中发挥有效的抗肿瘤作用。挑战在于保持对纳米颗粒的物理化学性质的控制,同时模拟细菌的免疫原性特征以激活免疫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细菌外膜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免疫刺激剂出现,当与纳米颗粒整合时,可以微调其物理和化学属性,从而产生细菌膜包被的纳米颗粒(BM-NP)[148]。Gao等人[149]使用大肠杆菌作为模式生物,用细菌外膜包被纳米颗粒,产生BM-NP。通过小鼠体内实验,这些BM-NP证明,与单独使用细菌外膜相比,其激活树突细胞、刺激抗体产生和诱导针对大肠杆菌感染的T细胞应答的能力显著增强。Wang等人[150]诱导细菌分泌细胞外基质形成天然生物膜,包裹益生菌,显著提高了小鼠和猪的胃肠道耐受性和粘膜粘附性。此外,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的小鼠中,这种方法导致显著增强的去定殖效果。
基于细菌的DSS在研究和临床试验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然而,它们在实际临床应用中不断遇到挑战,包括扩大生产规模、增强药物递送过程中的细菌存活、精确控制细菌定殖、剂量确定和潜在的生物安全问题。研究人员致力于通过生物和化学工程策略拓宽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范围[139]。
2.2.5. 生物颗粒递送载体
各种生物颗粒,如病毒样颗粒(VLPs),作为RNA递送的有效载体,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关注。构成病毒外壳的病毒结构蛋白可与 RNA 包装信号(PS)发生天然的相互作用,并促进RNA以VLP的形式在细胞间转移。但这种衣壳蛋白与逆转录病毒(如HIV-1)的结合特异性不是特别强,也可以包装其他RNA分子。通过融合RNA结合蛋白或将特异性识别序列整合到RNA分子中,可以提高VLPs对RNA分子的选择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可能会干扰VLP的装配或分泌过程。
Segel等人[151]鉴定了一种内源性蛋白PEG10,其能够从人细胞形成VLP,并优先结合和促进其mRNA的囊泡分泌,选择性包封和递送其他RNA。利用人类PEG10,他们开发了一种包装、分泌和递送特定RNA的系统,称为选择性内源性细胞递送封装(SEND)。该系统源自人类病毒,引发的免疫反应比现有的病毒载体和脂质纳米颗粒更小,它可以高效地将基因编辑工具递送到小鼠和人类细胞中,实现对目标基因的编辑。由Banskota等人开发的EVLP已证明其在人类和小鼠细胞以及小鼠的各种组织和器官中以极低的脱靶率介导高效碱基编辑的能力。这一创新系统有效地整合了病毒和非病毒递送方法的关键优势,将其定位为治疗性大分子递送的有前途的候选者[152]。
内共生细菌是一类特殊的微生物,能够寄生于宿主细胞并分泌调节宿主细胞的生物因子,已经进化出复杂的递送系统。一种这样的系统是细胞外收缩注射系统(eCISs),一种将携带的蛋白质注射到真核细胞中的类似注射器的大分子复合物。Kreitz等人[153]选择来自Photorhabdus asymbiotica(Photorhabdus virulence cassette,PVC)的eCIS用于他们的研究。PVC系统有可能被重新编程以将各种蛋白质递送到人和小鼠细胞,在基因治疗、核酸递送和生物控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仿生给药系统继承了天然载体的优良特性,是生物载体与功能剂的高级集成。改性后,这些系统还表现出改善的渗透性、承载能力和特异性[154]。目前,仿生给药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包括其体内作用机制的阐明、体外修饰技术以及药物负载对系统本身的影响。此外,细胞膜的分离和纯化仍然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155]。在有前景的仿生给药系统中,混合细胞膜因其延长的循环时间和主动定位特性而脱颖而出[156]。随着研究的深入,仿生给药系统有望成为高效、靶向给药系统的理想候选者。
参考文献
1. Nat. Biomed. Eng. 2021, 5, 951–967.
2. Cancers 2021, 13, 3387.
3. Acta. Biomater. 2019, 85, 1–26.
4. Mater. Today. Bio. 2021, 12, 100154.
5. Nanoscale Res. Lett. 2013, 8, 102.
6. Annu. Rev. Anal. Chem. 2008, 1, 801–832.
7. Curr. Med. Chem. 2004, 11, 199–219.
8. J. Pharm. Sci. 2001, 90, 667–680.
9. Curr. Med. Mycol. 2021, 7, 71–78.
10. J. Drug Target. 2021, 29, 754–760.
11. Int. J. Nanomed. 2020, 15, 5783–5802.
12. Adv. Mater. 2018, 30, 1704–1734.
13. Int. J. Pharm. 2014, 474, 6–13.
14. Adv. Mater. 2022, 34, 2107–2121.
15. Mater. Rep. 2020, 34, 516–522.
16. Vet. Parasitol. 2020, 283, 109186.
17. J. Control. Release 2019, 307, 247–260.
18. Lancet Microbe 2023, 4, e20.
19. Memórias Inst. Oswaldo Cruz 2016, 111, 330–334.
20. Fungal. Biol. Biotechnol. 2021, 8, 22.
21. Nat. Nanotechnol. 2020, 15, 313–320.
22. Nat. Protoc. 2023, 18, 265–291.
23. Nat. Mater. 2021, 20, 701–710.
24.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2, 119, e2116271119.
25. J. Am. Chem. Soc. 2023, 145, 4691–4706.
26. Nat. Nanotechnol. 2017, 12, 813–820.
27. Science 2022, 375, 91–96.
28. Chin. J. New Drugs 2022, 31, 2109–2113.
29. Nano Lett. 2020, 20, 4264–4269.
30. Nat. Commun. 2019, 10, 5783.
31. Pharmaceutics 2022, 14, 778.
32. Nat. Rev. Drug Discov. 2021, 20, 101–124.
33. Biomater. Sci. 2022, 10, 1883–1903.
34. Int. J. Pharm. 2017, 528, 381–382.
35. Molecules 2020, 25, 638.
36. Ann. N. Y. Acad. Sci. 2004, 1031, 405–411.
37. Clin. Exp. Pharmacol. Physiol. 2010, 37, 587–592.
38. Int. J. Oncol. 2009, 35, 1277–1288.
39. J. Pharm. Sci. 2021, 111, 1937–1951.
40. Heliyon 2023, 9, e21794.
41. Int.Immunopharmacol. 2003, 13, 1699–1714.
42. J. Drug Target. 2023, 5, 21–28.
43. Epilepsia 2021, 62, 90–105.
44. Polymers 2021, 13, 4400.
45. Mol. Pharm. 2008, 5, 505–515.
46. Nanomaterials 2020, 10, 847.
47. J. Control. Release 2022, 353, 229–240.
48. J. Control. Release 2012, 161, 795–803.
49. ACS Nano 2014, 8, 2134.
50. J. Control. Release 2017, 249, 173.
51. Int. J. Mol. Sci. 2017, 18, 628.
52. Nano Lett. 2018, 18, 6207–6213.
53. Chem. Eng. J. 2024, 480, 147951.
54. Nat. Mater. 2023, 22, 391–399.
55. Eur. Polym. J. 2021, 143, 110179.
56. Carbohydr. Polym. 2016, 136, 630–640.
57. ACS Nano 2018, 12, 8893–8900.
58. J. Control. Release 2021, 334, 64–95.
59. J. Control. Release 2021, 332, 312–336.
60. Adv. Drug Deliv. Rev. 2020, 156, 80–118.
61. Int. J. Pharm. 2006, 307, 93–102.
62. J. Mater. Chem. 2020, 8, 1672–1681.
63. Eur. J. Pharm. Biopharma. 2023, 184, 159–169.
64. Carbohydr. Polym. 2023, 303, 120439.
65. J. Control. Release 2017, 263,112–119.
66. Biomaterials 2013, 34, 5640–5650.
67. Adv. Funct. Mater. 2016, 26, 4201–4212.
68. Shandong Chem. Ind. 2018, 47, 58–60.
69. Ann. Biomed. Eng. 2016, 44, 2049–2061.
70. Angew. Chem. Int. Ed. Engl. 2023, 62, e202212866.
71. Bioact. Mater. 2024, 32, 149–163.
72. Adv. Mater. 2021, 33, e2007910.
73. Molecules 2020, 25, 2505.
74.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23, 15, 26273–26284.
75. Pharmaceutics2020, 12, 219.
76. Prog. Vet. Med. 2023, 44, 121–126.
77. Molecules 2021, 26, 5905.
78. J. Control. Release 2022, 348, 206–238.
79. Pharmaceutics 2020, 13, 24.
80. Biomaterials 2021, 275, 120970.
81.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6, 8, 11288–11297.
82. Adv. Mater. 2019, 31, e1904997.
83. Vet. Comp. Oncol. 2017, 15, 1537–1542.
84. Appl. Surf. Sci. 2015, 332, 62–69.
85. Plast. Rubber Compos. 2018, 47, 273–281.
86. Front. Microbiol. 2023, 14, 1293363.
87. Comp. Clin. Pathol. 2020, 29, 369–374.
88. Int. J. Mol. Sci. 2019, 20, 1672.
89. Brain Res. 2020, 1734, 146738.
90. J. Nanobiotechnol. 2021, 19, 31.
91. Nat. Commun. 2015, 6, 10066.
92. Saudi Pharm. J. 2014, 22, 223–230.
93. Drug Deliv. 2020, 27, 585–598.
94. Acc. Chem. Res. 2019, 52, 1255–1264.
95. J. Zhejiang Univ. Med. Sci. 2023, 52, 318–327.
96. Small 2021, 17, e2006484.
97. Biomaterials 2020, 254, 120142.
98. Drug Deliv. Transl. Res. 2023, 13, 716–737.
99. Theranostics 2015, 5, 863–881.
100. Anti-Cancer Agents Med. Chem. 2022, 22, 2255–2273.
101. Chin. J. Pharm. 2023, 54, 496–503.
102. Nat. Commun. 2019, 10, 3452.
103. Nat. Biomed. Eng. 2017, 1, 0011.
104. Adv. Mater. 2018, 30, e1802233.
105. Theranostics 2020, 10, 1281–1295.
106. Nat. Biotechnol. 2022, 40, 1250–1258.
107. Nat. Chem. Biol. 2021, 18, 216–225.
108. J. Leather Sci. Eng. 2022, 4, 31.
109. Adv. Mater. 2022, 34, e2206861.
110. Cancers 2019, 11, 1836.
111. Drug Discov. Today 2023, 28, 103514.
112. ACS Omega 2020, 5, 995–1002.
113. Adv. Drug Deliv. Rev. 2018, 130, 12–16.
114. J. Neuroimmune Pharmacol. 2020, 15, 487–500.
115. Matter 2023, 6, 761–799.
116. J. Drug Target. 2020, 28, 129–141.
117. Cancer Med. 2022, 11, 4979–4988.
118. Adv. Drug Deliv. Rev. 2013, 65, 357–367.
119. Int. J. Mol. Sci. 2020, 21, 367.
120. Anal. Chem. 2019, 91, 14036–14062.
121. Mol. Pharm. 2022, 19, 3042–3056.
122. Nat. Commun. 2018, 9, 1305.
123. Int. J. Nanomed. 2023, 18, 4751–4778.
124. Biomaterials 2020, 242, 119952.
125. JACC Basic Transl. Sci. 2023, 8, 457–459.
126. Semin. Cancer Biol. 2023, 96, 64–81.
127. Mol. Cell. Biochem. 2019, 495, 1–6.
128. Hum.Gene Ther. 2015, 26, 452–462.
129. J. Control. Release 2016, 244, 139–148.
130. FEBS Lett. 2014, 588, 3954–3958.
131. Nat. Biotechnol. 2016, 34, 328–333.
132. Nat. Biotechnol. 2021, 39, 691–696.
133.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1, 118, e2017925118.
134. Mol. Ther. 2023, 31, 2914–2928.
135. Adv. Mater. 2023, 35, 2212210.
136. Chin. J. Pharm. 2018, 49, 1041–1052.
137. Nat. Commun. 2021, 12, 6116.
138. Science 2022, 378, 858–864.
139. Adv. Mater. 2021, 33, e2102580.
140. Nano Lett. 2016, 16, 3493–3499.
141.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0, 117, 22473–22483.
142. PLoS Pathog. 2011, 7, e1002145.
143. Nat. Rev. Microbiol. 2010, 8, 340–349.
144. Infect. Immun. 1990, 58, 1429–1436.
145. Infect. Immun. 1996, 64, 4680–4685.
146. Infect. Immun. 1995, 63, 1827–1834.
147. Br. J. Biomed. Sci. 2002, 59, 183–190.
148. PLoS ONE 2015, 10, e0144559.
149. Nano Lett. 2015, 15, 1403–1409.
150. Sci. Adv. 2020, 6, eabb1952.
151. Science 2021, 373, 882–889.
152. Cell 2022, 185, 250–265.
153. Nature 2023, 616, 357–364.
154. Vaccines 2015, 3, 814–828.
155. ACS Nano 2021, 15, 19756–19770.
156. Clin. Transl. Med. 2021, 11, e292.
本文转载自百奥信康公众号(ID: BioScenePhar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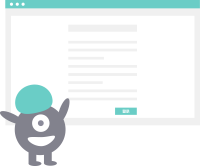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33011002015279
浙公网安备33011002015279
 本网站未发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戒毒药品和医疗机构制剂的产品信息
本网站未发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戒毒药品和医疗机构制剂的产品信息
收藏
登录后参与评论